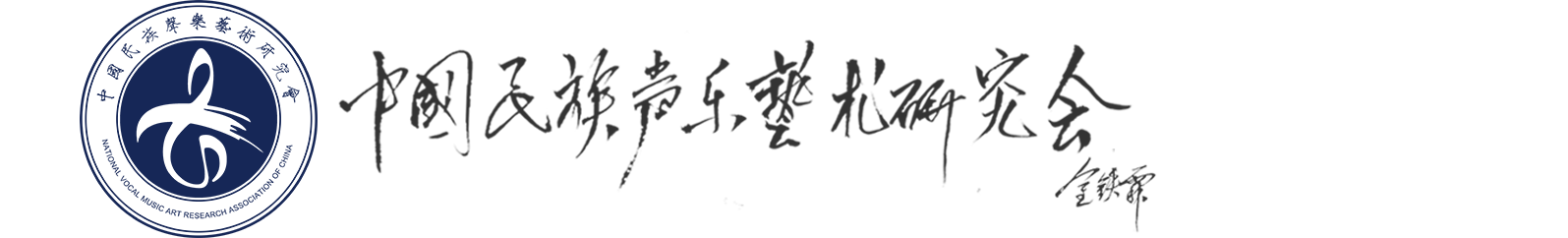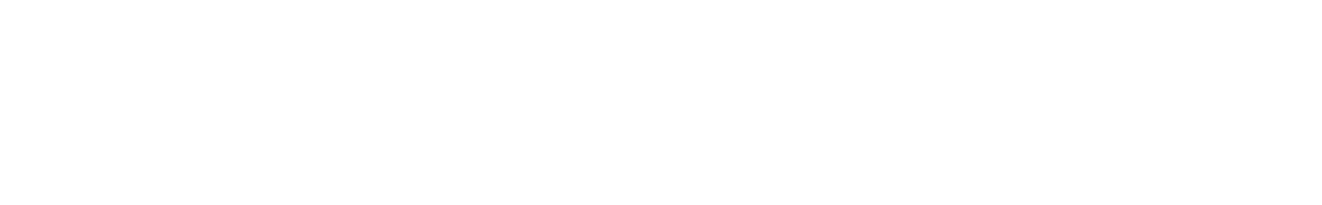- 新闻动态
中国少数民族声乐艺术的定位与发展 杨曙光
中国民族声乐艺术,是一个涵盖极广的艺术概念。但是,目前关于这一概念的界定(理解)与实践,实际上大都建立于欧洲与汉民族音乐文化的理论基础上,而且与之相关的价值判断仍然是相当偏颇的。中国是个多民族的国家。各民族由于生产方式,历史背景,语言差异以及风俗习惯的不同,从而形成了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各具特色的音乐文化。没有对少数民族声乐艺术真实、全面的认识与实践, “中国民族声乐艺术”这一概念将是不全面和不完整的。

作为中国民族声乐艺术的组成部分,中国少数民族声乐艺术在“民族声乐艺术”中处于什么位置呢?长期以来,少数民族声乐教学,大多采用美声唱法和汉民族民歌的教学模式,对唱法技巧的重视,远远超过对民族风格特征的重视和尊重,甚至用某种模式整个取代少数民族声乐教学,使很多演唱者失去了风格纯正地演唱本民族歌曲的能力。这种概念混淆,唱法单一,千人一腔的现象,只能是艺术品格幼稚或艺术风格衰落的表现。
现实存在的艺术从来不是单一标准的。艺术不是批量生产的工业品,如同人人穿西服或人人穿马褂,艺术还有什么魅力可言呢?因此,突出艺术个性,尊重风格差异,中国民族声乐艺术才能在世界民族艺术之林中找到自己的位置。本文欲通过对中国少数民族声乐艺术同汉民族声乐艺术的比较,来认识和分析少数民族声乐艺术的文化内涵,以及它的特殊性和价值标准,从而找到其准确的定位座标。由于笔者理论水平有限,文中必然存在浅谬之处,敬请读者指正。
一、少数民族音乐文化的独特性
声乐艺术必须通过“唱”这个特殊行为来表情达意。然而,“唱”这种行为必然建立在特殊的文化内涵这个基础之上,只有在这个基础的承载下,这种特殊的艺术行为才有意义。如果割断了唱法与其特殊文化背景的联系,它就必将成为“无源之水”。因此,在论述中国少数民族声乐艺术时,首先应分析一下少数民族音乐文化的特质。
在人类文化的建构中,艺术是最能够鲜明地体现文化的特异性和独创性的。在今天,由于工业文化强大的物质驱动,使世界文化呈现出暂时的同一性发展趋势,这就使得文化的特异性体现出对于艺术之未来发展的积极价值。因为,如果世界诸文化的差异性趋于消失,亦即世界各文化同化成为一种单一模式,那么,人类的存在就会失去其精神的丰富和生动——这也是民族艺术表现的特异性越来越被重视的原因所在。近年来,侗族大歌在法国巴黎的轰动演出,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这不仅是异文化听众对这种表现形式的理解和认同,而是作为欧洲文化传统载体的欧洲人,从这种独特而陌生的东方音乐文化之中,认识到了一种他们不熟悉的,但同样生动和深刻的情感和思维方式。他们通过这如“清泉闪光般的歌声”,解读一个万里之外陌生民族的心灵。这实质上是一次文化间的互相沟通,互相理解和互相的价值肯定。由此,我们可以断言,奠基于特定民族文化特质的声乐演唱行为,才更能体现人类音乐的文化本义。
中国是一个拥有56个民族的国家,各民族适应其各个不同的生存环境。选择适宜的经济生产方式,或农耕、或游牧、或半耕半牧、或渔猎采集。他们为了适应这种经济生产方式,进而创造出一整套特殊的文化思维和社会生活方式,包括风俗习惯,道德法规,家庭结构、社会政治组织、社会制度以及与之相适的意识形态和宗教信仰。在历史发展中,他们不断地调整、丰富,并越来越习惯于这种土生土长的文化模式,在行动中遵守它,在心理上依赖它。虽然任何一种文化模式都存在历史的局限性,但其存在却促成了民族音乐文化与其生态环境的和谐与共生。俗话说,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在中国北部和西南部草原上,牧区的民族喜欢骑马,住毡房,喝奶茶或酥油茶等特点,这是由于牧区气候寒冷,牧民长期逐水草而居的特点和历史传统决定的;而在这些游牧民族中产生和存在的音乐文化,则与其特异的自然与文化生态密切相关。如反映游牧生活的歌曲,有蒙古族的“长调”,鄂温克族的“扎恩达勒格”、鄂伦春族的“赞达仁”以及哈萨克族,柯尔克孜族的牧歌等。这些曲调缓慢悠长,辽阔而深沉,具有浓厚的草原气息,它们与这些民族萌生于其环境与文化的时间观、空间感和节律感、以及其情感方式等,均有血肉相连的因果关系。又如我国少数民族最多的云南省,由于其地理环境的特殊性,从海拔70多米到近7000米的“立体”生态分布,和从热带雨林到高寒山地的“立体”气候,孕育和保存了形态极为多样的各民族文化及其音乐行为与风格样式。 “如纳西古乐温文尔雅的懦学风范,瑶族经腔神秘诡奇的道家法度,藏族法乐凛然威严的密宗气息,傣族“依拉灰”圆润通和的上座部佛教色彩,怒族祭歌古朴原始的民间信仰韵味……” (周凯模《云南民族音乐的背景及文化结构》)在这些民族的文化来源和传统各异并存共生的漫长历史进程中,顺水行、依山走、互动互融,逐渐形成了相对独立而又并存的局面,构成了多层次特殊而丰富的民族异质文化群。正是这些特殊的文化地理条件,使各民族在适应自然,把握世界的过程中,建构了不同的生存环境和文化体系,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音乐文化赖以滋生与存在的土壤。
少数民族的音乐与汉族音乐既有一定的联系和共同点,也有许多本质性差异,与西方艺术音乐就更是相去甚远。如从音乐“表演”方式和文化功能角度看,汉族音乐中有很大部分是带有表演性质的音乐,如戏曲音乐,大部分说唱音乐;而西方十八、十九世纪的艺术音乐则更是由专业人员表演,供一定社会阶层审美、娱乐或进行阶层文化认同的特定音乐种类。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则往往具有较为复杂的文化功能性,对他们来说,单纯的“审美”艺术是不存在的,由于无文字等一系列的因素,他们的音乐必须要承担一系列文化功能,如传承知识,讲述历史等等。如蒙族的《江格尔》、藏族的《格萨尔王传》,维吾尔族的《艾力甫与赛乃姆》等,就是这些民族的音乐化的历史知识教材。少数民族音乐又往往是信仰传播的工具,如满族、锡伯族、赫哲族的“萨满调”,彝族的“毕摩调”,拉祜族和佤族的“摩巴调”等。诚如一位侗族歌手所说,她们学唱侗族大歌就象汉人在学校学知识一样重要,这可以看作对少数民族音乐的独特意义的通俗表述。
总之,特殊的生态环境和独特的人文传统,为少数民族本土文化提供了深厚的文化内涵,由此而产生的民族音乐文化的个性,则表现为少数民族音乐的具有特殊适应性的文化特质。那种认为少数民族音乐文化原始,简单,落后的说法,本身即是简单,武断和自以为是的肤浅之论,当人们认真地去考察、比较、认识它时,犹会感到它内涵的丰富,魅力的诱人,形态的成熟及存在的合理性,同时,还会发现它包含着许多发展的生机,可以在文化交流,融汇与再创造中获得新的,更胜以往的繁荣。
二、少数民族声乐艺术的差异性
在我国声乐界,往往有人把“美声唱法”看做来源于意大利的同一模式和同一风格的艺术,而不注意除意大利外,西欧各国唱法中彼此不同的民族特点,比如俄国、德国、法国等其它各国的风格各异的唱法。同样,把“中国民族唱法”看做是仅限于汉语人群的“汉民族唱法”,忽略了汉民族与其他民族在演唱方式上的差异。众所周知,处于青藏高原的藏文化生态环境中的藏族民歌,和处于湘西大山沟里苗文化生态环境中的苗族民歌,以及汉民族文化环境中汉族民歌,在演唱方式上各有其模式化的特征系统,其形态以至价值内涵都差异甚巨,故不可一概而论。中国少数民族声乐艺术的多元、兼容、独特的艺术个性和民族特质,应该是“中国民族唱法”不可缺的题中之义。然而,少数民族的演唱方式具体而言有哪些特点呢?
1.关于演唱
演唱的物质基础是人的发声器官及其运动,表面看来,人体发声器官的生理结构,无论什么民族,都应是大体相似的,但各民族嗓音或发音方式都是有差异的。从语言学或语音学角度看,中国南方各民族语言分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壮侗语族、苗瑶语族、以及部分阿尔泰语系和南亚语系的语言等。不同的语系(语族)语种乃至方言土语群,都有不同的发音方式,或习惯使用不同的发音部位发音,这就必然造成不同语言(语音)人群发声习惯、及对人声评价标准的不同。这些不同当然会对音乐演唱方式和评价标准产生影响。例如,各民族的某些特色性歌曲,其发音部位和发声方式,是外民族难以模仿和评价的,如蒙族、纳西族、傣族、侗族的颤音,彝族的小嗓等的使用,都鲜明体现出基于语音特质的声音形态与价值观的独特性。
我们较为熟悉的蒙古族长调“诺古拉”唱法,是蒙古族最具代表性、也最具风格特色的演唱技巧。 “诺古拉”即颤音,是指一种包括不同音高、拖腔丰富的装饰性歌唱技巧。由于蒙古族语言和发音部位不同,至使这一唱法与汉民族唱法相比,无论在音色上还是演唱评价上,都不是汉民族唱法所能替代的。蒙古族的“诺古拉”比汉民族的“颤音”更峤曲细密,形成听觉中更多更复杂的韵律韵味,这跟蒙古族语言有关。因此,如果不会说蒙语或不懂蒙语的人,就很难进入长调歌曲的深邃内涵。
“诺古拉”的演唱,由于发音部位(颤动部位)不同,音区、音域的高低不同,其演唱技巧多达七八种,但经常运用的是三种:(1)额柔诺古拉,表现为下巴颤动。 (2)唐乃诺古拉,表现为上腭颤动。 (3)好莱诺古拉,表现为咽部颤动。长调歌唱家哈扎布,是一个被公认为唯一的、掌握了所有“诺古拉”技巧的歌唱家,他的演唱风格以“额柔诺古拉”为主要标志,表现为下已松驰、灵活,使诺古拉可以自由运用,音乐形象舒展深沉,具有丰富的表现力。著名女高音歌唱家宝音德力格演唱的呼伦贝尔长调则热情奔放,激越高昂,带有嘹亮透明的色彩。她的这一演唱风格主要是善用“好莱诺古拉”,即声音在咽壁肌肉的横向颤动与纵向颤动结合中产生的。她说, “要让咽壁灵活地颤动,小舌与软鄂的松驰是至关重要的”。由此看来,颤音的自由运用和由此形成的丰富的音律和音色,是蒙古族长调演唱中的主要风格特点,也是他们评价一个歌手唱得“好”与“不好”的基本标准之一。
长调的曲调舒缓而悠长,由于其歌词较少,大多曲调都表现为在华彩音和诺古拉的拖腔,这与汉民族的“字正腔圆”唱法及其标准不同。长调的旋律进行特点恰恰是歌词与“腔”的分离,长调以旋律为表现情感的主体,不受词的限制,语言的表现功能在此是第二位的。正因为如此,当人们在感受长调拖腔的自由律动时,同时也在感受“诺古拉”的独特表现力,感受这种唱法独有的亦即不可代替和不可(被外文化标准)评价的美学品质。演唱者即兴自由的“诺古拉”颤动,因此,而具有辽阔的草原气息,透射出蒙古族人所特有的审美标准和独特的音乐感觉。
仅从蒙古族“诺古拉”唱法一例,我们可以看到,所谓“中国民族唱法”应是一个内涵与外延极其丰富的概念。这个唱法所涵盖的种类、形态、功能和价值,不仅多样并存,而且不可互替;它们各有其“美的”、 “科学的”、 “有用的”独特评价标准与存在理由,因而彼此间并不存在“原始与现代”、 “先进与落后、 “高级与低级”、 “科学与非科学”等进化差距。对于某个民族的唱法,你可以不熟悉它,甚至不喜欢它,因为每一个人都是特定文化环境的产物,不得不禀承这个特殊文化的艺术价值观,形成特殊的艺术审美趣好。但是,我们不能因此而抑我所疏,扬我所亲,用某一种唱法标准去衡量无穷的唱法种类。倘若如此,我们的专业声乐教学就会不自觉充当民族声乐艺术的阉割者角色,为中国音乐的未来辛苦地营造一个风格生态危机重重的萧瑟局面。
2.关于用嗓
与汉民族的演唱相比,少数民族声乐在用嗓的力量,真假声的比例“配方”,以及共鸣腔的运用上存在许多差异。有许多民族在用嗓上(由于审美习惯的原因)只用部分共鸣,因此,在共鸣腔体的运用上,用上部头腔,中间口腔还是下部胸腔,是区分用嗓的几个方面。总之,嗓子的用法可以有各种模式,共鸣状态的选择也可以有所不同,从语言发音的形状以及用嗓发声的形态,就可以区别出它们之间的差异。
(1)苗族的爆破音
湖南湘西的苗族,属于汉藏语系的苗谣语族。由于受语言的制约,如塞音、塞擦音、边音、喉塞音、舌尖齿龈音等,形成了它独具特色的发声法。一般来说,湘西苗族人说话都较为低沉浑厚,以母音起首的音节常常带有喉塞音。因此,在演唱时口腔共鸣多于头腔共鸣,以咽喉为中心,上下真假声结合是苗歌演唱的特点。如《苗家酒歌》。

注:《苗语——请喝一杯苗家米酒。△——用假声演唱 ※——用真声唱。
用真声演唱时,声音是在喉音上作形,发出一种特殊的爆破音,这种听起来尤如两节的声音在汉民族的声音运用中是不允许有的,被称为是真假声打架的声音。但在苗歌演唱的运用中却成了一种非常有韵味的风格。从发声效果看, “假声”演唱是通过声带缩短、变薄、声带边缘振动所致。这种声音振动面积较小,发音位置较高,故声音好像是悬浮于头顶。而真声演唱,唱者能清晰地感到声带的声音,即环甲肌与甲披裂肌对抗的声音,声带局部振动,面积较大,故声音丰满,具有磁性感。苗族爆破音的演唱,就是建立在“真声”基础上的特殊用法,在一定的声区范围内,是声带局部振动和边缘振动的产物。笔者曾采访过湘西苗族最著名的民歌演唱家张云珍同志,她演唱了地道的苗歌,的确是用嗓独特,声音含蓄迷人,委婉动听,在她六十多岁的年龄里,有如此漂亮的声音,不能不感叹少数民族声乐的特殊性和科学性。她是懂得一些声乐知识的,她认为,苗歌里喉音的运用,真假声交替演唱都是苗歌用嗓的特殊需要,一定要保留,但这种声音要把握自如,想用时召之即来,或者挥之即去。 “我演唱这种爆破音时,在喉头上碰一下就离开,既保持了风格和音色,又使声音符合发声规律”。想必,这就是她声音青春长驻的秘密吧。
(2)土家族的“打喔嗬”
位于湘鄂西的土家族,由于地区山多人稀,人们居住分散,出于远距离声音联络的需要或习惯,歌手们唱歌时常用呐喊式发声模式,因此,在用嗓上形式了声音高亢,音量强大,富有穿透力的演唱特点。 “打喔嗬”是土家族山歌演唱中十分常见的,类似呐喊的典型衬腔现象,是山歌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由于“喔嗬”的功能是至远性的,从演唱实践看,它的用嗓方式具有符合目的(至远)的充分合理性(或日“科学性”)。
我们知道,声带是通过拉紧,靠拢,缩短,变薄而振动发音,声带的拉紧主要是靠环甲肌和披裂肌相对抗用力,两声带的靠拢是靠破裂肌群的力量。由于环甲肌与破裂肌两肌肉群工作时用力情况的变化,致使在歌唱时声带要随着音高的变化而做出相应的调节。如“喔嗬”的开头音为“U”母音,随着音的升高,声带逐渐收缩变短,在咽腔作形的基础上,口形逐渐向“0”靠近变形。其过程是,唇形在保持圆的状态下,口形从小过渡到稍大,抬软鄂,舌位放平,咽部上提,同时咽壁站定,头腔打开,使其演唱达到尽可能圆润、高亢的目的。 “打喔嗬”的主要母音是“u”“0”,嘴是撮合的,由于“UO”字母本身具有混声色彩,因此, “打喔嗬”的用嗓是混声的,即真假声结合的。共鸣腔的运用也是随着音高的部位变化,彼此间互相渗透的。没有与之相适应的发声方法,声音的至远性是不能成立的。 “打喔嗬”是演唱土家族山歌的一种基本功,无论是高亢挺拔声震山谷的“喔嗬”声,还是优美的“嗬嗬也嗬嗬也”的衬腔,其发声方法本身和其目的性,都是充分合理的,因而值得研究和采纳的。
3.关于润腔
这里所说的润腔,不是指汉民族的“装饰性润腔”,而是指少数民族特有的“特色性润腔”,即特殊的演唱技巧、特殊的音色和特殊的风格。它是建立在各民族不同语言,不同发音,不同用嗓的基础上的。比如前面所提到的蒙古族的“诺古拉”,苗族的“爆破音”,土家族的“打喔嗬”等等,我们很容易从听觉上区分它们之间演唱技巧、音色和风格上的差异。再如,同样是颤音,我们也不会把汉族唱法的装饰性颤音,跟蒙族,傣族,侗族唱法的颤音彼此混淆。各民族的歌唱润腔方法,是构成其音乐艺术风格的最重要因素之一,因而也是不可互替的,和不能用单一标准衡量的。
藏族是我们非常熟悉的民族,其民歌形式多样,音乐丰富多彩,所用的特殊润腔技巧也是琳琅满目,如“整固”、改变母音、真假声交替、爆破断音及滑音装饰音等。
“整固”是一种跳音演唱技巧的藏语名称,是藏族民歌中最具特色的润腔技巧。在演唱时,跳音音群中的第一个音在重复前面音的基础上,往下二度和三度弹跳,并在之后的稳定长音上二度弹跳,气息流畅,横隔膜弹跳自如,声音在喉部作形,并在咽喉上发出一种音色较暗的,似断非断,断中有连的声音效果,使旋律增添了生动活泼的动态效果,以及丰富多彩的音色变化,同时,也给旋律的推进增加活泼动力。如: 《在北京的金山上》中的第一句:

著名歌唱家才旦卓玛在演唱这首藏族歌曲时,运用了大量的“整固”技巧,并且灵活自如,恰到好处,在音色上和风格上有看鲜明的特色。 (常留柱《藏族民歌及演唱技巧》)、这种叫作“整固”的润腔方式,与汉民族弹跳音演唱有很大差异。汉族弹跳音演唱追求声音高位置,音点较小,颗粒性较强,而“整固”演唱,声音是在喉部作形,声带摆动幅度较大。这两种润腔方式的差异既是文化的一一产生并认同于特定的文化人群,又是风格的一一体现出不同的音乐美感。因此,它们应该是得到同等的尊重,珍视和传承。
总之,中国少数民族声乐艺术,是中华民族音乐艺术的瑰宝。由于各民族在发音和用嗓上的差异,形成了丰富多彩的演唱形式,为世界声乐艺术提供了大量可资借鉴的宝贵范本。它不属于西方“美声”体系,也不属于中国传统声乐的“正宗模式”。无论从观念形态上,还是从形式结构,甚至传承方式方面,都是独具特色的。少数民族声乐艺术,在演唱上独特的风格和色彩,是其它声乐艺术体系不可替代的和无法评价的。
三、少数民族声乐艺术价值标准的相对性
中国少数民族声乐艺术作为“中国民族声乐”的组成部分,在多年的实践中,理论性关注很少,或者说至今没有从更高的理论层面与深度上来认识它们。这从常常见诸于主流评价的“简单的”、“落后的”、 “不科学的”等的判断上就可以见一斑。一些人或可认同它们的特质,但不能把它们作为一种完整的艺术形式来看待,而仅仅着眼于题材或素材的应用。有的人虽然能意识到各少数民族声乐艺术的意义和价值,但仍不自觉地用现行的西方传统音乐理论来认知它们,改造它们,其实质还是认定少数民族演唱方法的不“科
学”性。因此,制造了一大批以“美声”唱法为基础,以“汉族”民歌唱法为主体的所谓“民族唱法”歌手。这些歌手来自不同民族或地区,但在这种标准化教育的“规范”下,其原生背景赋于的本土音乐文化的演唱风格终归荡然无存,失去了其本民族音乐文化留在他们身上的气息,而成了专业声乐教育生产线上的、按照同一模式铸造的“标准件”。形成这一局面的原因,有对各民族文化和演唱缺乏了解、分析的因素,也有历史形成的偏见,以及在二十世纪以来“欧洲音乐中心论”的巨大影响等。归根结蒂,就其实质来说,价值观的偏颇,是首屈一指的问题所在。
承认不同民族的音乐应该有平等的价值观,这是我们分析少数民族声乐艺术特质的前提。音乐价值相对的观念包括三层意义:(1)人类不同文化的音乐其价值是相对的。 (2)不同文化的音乐,在传统价值体系上主要体现出差异性,因而是不可比的。 (3)衡量一种音乐文化的价值,只能用它所根植的那种文化采用的价值标准。这种思想的核心,就是认为,对任何文化所表现之价值的认识和评价,都取决于拥有该文化的民族对事物的看法;承认每种文化都有其独特的性质和充分的社会价值,否认欧美价值体系的绝对意义;认为全人类文化有本质上的共同性,但这种共同性往往通过不同的形式表现出来。
帕互络蒂就曾这样形容中国京剧: “京剧是一种很奇妙的表演……它以我们听起来相当压迫、不自然的声音演唱,然而,对他们来说,这样的音乐就和我们听普契尼一样优美动人。”这里实际上反映出审美趣好和文化背景的差异。中国少数民族的演唱也是如此,其问题的关键不是由谁(勿论是芸芸众生还是专家权威)来判定是否“落后”或“不科学”,而是以什么标准来判定“先进”与“落后”, “优秀”与“低劣”的价值观问题。如果认定只有欧式的或汉族式的“美声”唱法才有资格称为“优秀”,那么,各少数民族的演唱显然是“落后”了,可是,为什么一定要把洋的或土的或土洋杂合的“美声”唱法作为“先进”的标准呢?各民族都有自己创造的,能理解和应用于本文化整体的音乐文化,如前所述,中国少数民族音乐文化,无论从文化内涵,演唱形态,技法,品种,表演等都不亚于欧洲音乐和汉民族音乐,更重要的是中国少数民族声乐艺术自身体现的独特品格,深受各民族同胞的认同和喜爱。如才旦卓玛,胡松华,德德玛,克里木等各民族的优秀歌唱家以及中国少数民族歌手在国外演出的轰动事实,都证明了它们是有价值的。 (相反,有些人则对欧美模式的中国交响乐,歌剧,艺术歌曲等不太认同,这是一个值得探究与反思的现象)。显然,这一价值判断是来自各民族自己的文化标准。这就象蒙族人不能因为汉族人不熟悉蒙族的语言、民歌、长调以及“诺古拉”的演唱,就指责他们“落后”一样,那么,为什么要用“美声”唱法或某种唱法为标准来衡量中国少数民族声乐艺术呢?毕竟,音乐的价值要由它的拥有者来评价,他们对此自有其合理的标准。只有在思想上充分的尊重各民族的文化传统,承认各民族音乐文化的独创性和充分的价值,反对“欧美中心主义”,在实践中才能真正平等地对待少数民族的演唱艺术,而中国少数民族声乐艺术也才能真正寻找到自己准确的定位。
四、少数民族声乐艺术继承和发展的必要性
在声乐界,特别是声乐教学中,怎样处理好继承和发展的关系,是教学中非常重要的课题。从教学结果看,我们并没有很好地把握好这个关系。否则“标准化”地批量制造专业声乐学生声乐演唱风格这一不合理现象,就不至如此地普遍乃至司空见惯。众所周知,继承传统音乐文化,是发展民族音乐必不可少的先决条件,如果传统中断,就谈不上发展。放弃继承即放弃发展。试想,倘若我们数千年积累起来的少数民族音乐文化资源一旦失去,那么,我们所特有的“民族性烙E门”将从何而来,?“独特的音乐艺术品格和色彩”又从何谈起?中国少数民族声乐艺术还有什么“丰富多彩,光辉灿烂”的发展可言?如果少数民族演唱艺术进入院校教育后,仅仅循着某种审美价值方向发展而割断了它们与本身文化的联系,那么,它的发展将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必将成为无源之水,无根之木,演唱的艺术形式也必将变得串调乏味。
当然,少数民族声乐艺术与欧洲、汉族声乐艺术一样,也有其自己的局限性, “固步自封”地拒其它艺术于门外,也是不足取的。在发声技法上还是有必要借鉴包括汉民族和“美声”在内的所有外国唱法的经验,盲目地轻视和排斥异文化唱法的观念与做法都是不恰当的。比如在气息和共鸣腔的运用上就是如此。气息的基本功扎实了,演唱的生命力就长久,而比较好地运用共鸣腔体,可以丰满音色,扩大音量,表现力更丰富。在这些方面,美声唱法较为系统的理性认识和训练方法,可以对我们有一定助益(但绝不能全盘照搬)。
文化间的关系不应是对抗,而应是彼此尊重,相互借鉴和共同发展。这个观念已经为越来越多的人士所认识,这也是声乐艺术发展的必然趋势。学院教育由于师资水平,老师作为个体的认识限度,教材教学方式,教学设备等方面的现实局限,可能会对少数民族声乐艺术的传统纯正性有一定的影响,但这是不可避免的。只要把握住少数民族歌唱风格演变的“度”。不使其因演变而失去其基本的传统风格特征,那么,这一演变就可视作合理的发展。不过对这个“度”的把握应非常小心,来不得半点自以为是。贵州艺校侗歌班的教学模式就是一个比较成功的例证。他们保留.了“歌师传习”的侗歌传统教育方式,又加入了现代音乐理论性分析方法和知识,不但在教学中,按照现代教学方法讲步骤,讲理性,而且保持了侗歌艺术文化内涵的主要部分。另如中央民族大学音乐系教授糜若如先生,在少数民族声乐教学中较好地处理了民族特色和演唱技巧的关系,培养了蒙古族的乌日娜,苗族的扬琼,满族的卢捷等一批优秀的少数民族声乐演员。
由于文化内涵在不同的民族和不同的时代有着程度不同的差异性,因此,对中国汉民族以及西方声乐演唱方法和教育方法,都不应取教条主义态度,不论是借鉴或继承,都不能代替创造。今天,世界文化的大交流、大碰撞、大融合给每一种文化艺术形式都带来了融汇变异和发展的动力与机会,或许还有变化的压力。中国少数民族声乐艺术的发展,必须适应这个新的生存环境,在“变”与“不变”的动态平衡中求得生存与繁荣,可以这样说,二十一世纪将是世界各民族文化艺术多元化发展的世纪。那么,在文化多元化的整合格局中,中国少数民族声乐艺术也必须进一步加强自身音乐文化的继承和发展。只有向世界尽可能完整地展示包括中国少数民族音乐文化在内的中国多元一体的传统音乐文化,才能进一步促进我国的音乐文化走向世界,走向未来。
参考书
1.云南民族音乐的背景及文化结构——周凯模
《云南艺术学院学报》1997年2期
2.浅议美声唱法与蒙古族长调演唱的结合——王诗学
《心儿的歌唱》安徽人民出版社
3.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的专业音乐教育将如何迈向新世纪一赵志扬
《云南艺术学院学报》1997年增刊
4. 走向世界音乐艺术之林——隶日、寒山
《云南艺术学院学报》1997年4期
5.案例解剖:音乐学的知识,逻辑与学风——何晓兵
《云南艺术学院学报》1999年1期
6. 鄂西高腔山歌演唱技法研究——李万进
“心儿的歌唱》安徽人民出版社
7. 王品素声乐教学初探——朱凌云
《音乐研究》1998年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