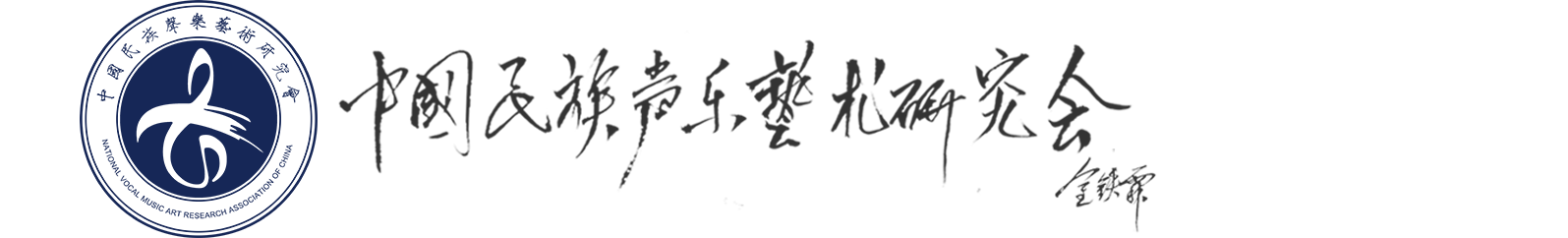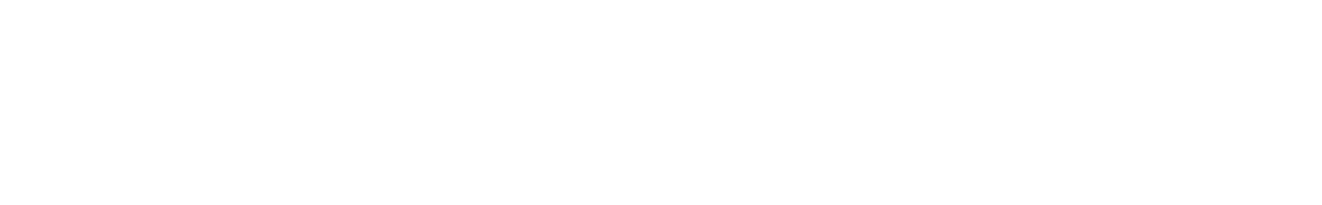- 新闻动态
声乐课堂随笔
作者:秩名 发布于:2017-08-18 04:57:06
文字:【大】【中】【小】
声乐课堂随笔
谭萍

金秋赏菊乐趣无穷,确是人生一大享受。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得到了超凡脱俗的恬淡心境,我虽没有五柳先生那般洒脱,却也从赏菊中得到了不少感悟和启迪。
看那菊花,不同的品种,不同的花色,不同的造型,不同的花期它们的形态几乎每时每刻都在发生细微的变化。那大朵的“大白积雪”、“云星黄鹤”、“醉舞杨妃”花色艳丽,花瓣肥厚,瓣瓣偎依,层层环抱,相互簇拥着宛若雍容华丽的贵妇人。另一旁的白色或浅黄色的一簇就迥然不同,不仅花色清淡而且花瓣细长,显得灵秀雅致,特别是顶尖部位略呈钩状,酷似古代妇人裙裾上临风的飘带,伸展开来是那么飘逸潇洒,婀娜多姿,活脱脱一个个楚楚动人的古典美人,无怪乎培养它们的花匠给它们起了“丝路花雨”、“千金一笑”、“黛玉葬花”这样俏丽的名字,仔细品味起来可说是惟妙惟肖了。就在人们不知不觉当中,那些似开未开的蓓蕾就像是电影升格拍摄的慢镜头一样,舒缓从容地绽露出它们娇羞的面容,让人搔首踟蹰、流连忘返。当然,引人入胜的不光是这些大“美人儿”,雏菊、悬崖菊等小朵的菊花也被花匠们别具一格地造就出各式各样的形象,一朵挨一朵多像是孔雀开屏,又像是一把把撑开的大花伞,再不就是那高出峻岭之上飞泻而下的瀑布,足以使人浮想联翩。
菊花原来不过就是一些野生的小花,经过几百年多少代花匠选种育苗、剪枝嫁接,精心地栽培,才培育出今天这么多的优良品种,如今它已被选定为北京市市花,为更多的人所赏识。
自然,我不是园艺家,我的这篇文章也不想论述花卉的栽培。不过,我想栽花和育人是同样的道理,做为一个声乐教师我要总结的是如何培养更多更好的声乐人材的问题。但是一提起笔来就自然而然想到了花,这大概是因为在很多场合被人们称做“园丁”的缘故。观花的归途上我常想,做为教师我们本来就应该是一名花匠,我们的工作就是为国家为人民培育妩媚多姿、色彩纷呈的“鲜花”当然不光是菊花(尽管菊花本身就包含了数不清的品种),还有牡丹、芍药、月季、蔷薇、玫瑰、芙蓉、腊梅、茶花、桃花……还有从国外引进的樱花、郁金香等等,等等。学生就像是一个个花骨朵儿,我们要给他们适时适度地“施肥、浇水”还要给他们“剪枝、除虫”,让他们在我们民族声乐这个大“花园”里,茁壮成长,“竞相开放、争奇斗艳”。
不知哪位名人说过这么一句话,“世上绝对没有完全相同的两片树叶”,学生也如此,存在着差别,我们只有承认这个差别,才能根据不同情况因势利导,有的放矢地制定教学计划,这就是古代圣贤提倡的因材施教。
由此我想到了已故的戏剧大师,著名的戏剧教育家王瑶卿先生,众所周知王瑶卿先生为中国戏曲的改革和发展做出了伟大卓绝的贡献,成就斐然,四大名旦皆出自他的门下。但他们不是王瑶卿的翻版,更不是王瑶卿的克隆。梅、尚、程、荀风格迥异,各有所长,形成了各自的流派,流传至今,对于京剧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我以为艺术教育不应该存在什么一成不变的“模式”,如果学生都像“一个模子磕出来的一样”那绝不是成功的教学。实践证明声乐教学没有“包治百病”的“仙丹妙药”,我推崇“一把钥匙开一把锁”,而这把钥匙就深藏在学生的心里。
有个别老师在教学不顺手的时候,很不情愿在主观方面,也就是在自己的教学方法方面找原因,总是爱抱怨学生的基础如何低,条件如何差。目的无非是为自己的无能进行开脱,借以掩饰自己的窘迫。殊不知他(她)这样做的结果将会极大的伤害学生本来就十分脆弱的歌唱心理,是非常要不得的,事实上,作为声乐教师,在学生身上找缺点,挑毛病,是再容易不过的事了。然而,如何发现学生的长处,优点,找出他们身上那被掩盖着的,常常被人忽视的闪光点,那微弱的、潜在却又十分难得的素质,将它小心地发掘出来,加以诱导、培育,造就成为有别于他人的特点和长处。这可就不是一件容易做到的事情了,但是我们必须做到。这是衡量一个声乐教师教学水平高低的重要标志。
歌唱家卡鲁索早在本世纪初就大胆地断言, “有多少个歌唱者就有多少种方法,同时,这些方法中的任何一种(即使用得再正确不过)也可能对其他任何人都是不适用的。假如有人想问我这样的问题,那我就要这样回答:即使我事实上是有一套特别的唱法,它或许也只适合于我一个人。”(引自《歌唱艺术》161页。)说到这里我要再一次重申我的观点:一个好的声乐教师就应该善于发现学生的特点,长处。在他(她)固有基础上,根据他(她)自身的条件,引导他(她)最大限度地展现自己的特长,开拓自己的艺术发展道路,以便于将来形成只属于他(她)自己的、独特的艺术表现风格。
我的具体做法是:
1.从头做起,打好基础
新生来自五湖四海,他们之中大多数嗓音条件好,音乐感觉也不错,尽管如此,在他们身上都不同程度地存在一些问题。我要求他们一切都要从头做起,我则根据每个人的不同情况有针对性地制定出具体的教学方案。
一、二年级的学生必须进行严格的、系统而又全面的声乐基础训练,使之具备扎实的声乐基本功。通过不同的练声曲、歌曲使学生气息平稳、呼吸畅通,腔体张开舒服而不撑(也就是打开腔体,顺通后咽壁上的管道),建立很好的、科学的发声习惯。用已故声乐教育家沈湘先生形象的说法就是:“制造一个优质的‘乐器’”。
在这个阶段多选用一些平稳易唱的初、中级教材,无论演唱中外艺术歌曲或歌剧咏叹调,都要和美声专业要求相同,声音连贯,气息平稳、流畅,腔体打开,真假声结合自如。首先必须要求学生
多听多看有关的经典资料,树立起正确的声音观念和识别能力。需要向学生反复强调,借鉴的前提在于学习,不学习就无从谈论借鉴。在这一阶段还要布置学生演唱我国历代传统的艺术歌曲(包括三十年代优秀的艺术歌曲)。在演唱中不仅要求气息好、声音好、共鸣还要求语言好,在这个基础上要求具备一定的表现力。
这个阶段有些学生会产生不同想法:“我是学民族声乐的,为什要唱这么多洋歌?”“我原来能唱《万里春色满家园》那么大的歌,现在光唱一些中声区多的《春思曲》、《你们可知道》(刻鲁比诺的咏叹调)……”等等。针对学生的思想问题,要做他们的思想工作,我对他们说:“要想盖一幢既华丽漂亮又结实牢固的大厦必须打好地基,只有优质的基础才能保证大厦的精美。”他们一旦学进去以后,尝到.了甜头,这时他们又会产生另外一种想法;“我干脆唱美声吧,.老师和同学都觉得我美声唱得不错。”这时我又要给他们做工作,告诉他们学通科学的唱法,为我们民族声乐事业添砖加瓦才是我们的最终目标。为了这个目标,我们要付出毕生的精力。
一、二年级基础训练阶段,无论男女哪个声部,都有相通的共性,那么在三年级后我认为就必须培养学生鲜明的个性。
2.承认差异,因材施教
在众多学生当中,他们的形象不同;有高有矮,有胖有瘦;他们的声音不同;有的嗓门儿大,又宽又亮,有的嗓门儿虽不大,但音色甜美,还有一些学生尽管嗓音条件一般,但唱得很有韵味。此外还有其它一些差异、诸如每个人的个性不同,审美习惯不同,等等。正因为存在以上诸多不同,才形成学生在歌曲演唱中表现出来的不同风格;有的实大声洪、痛快淋漓;有的委婉细腻、柔美动人。
三年级以后,要教学生继承我们民族声乐的传统唱法,特别是戏曲(京剧、豫剧、河北梆子等)。记得35年前,中国音乐学院歌剧系建系时,马可院长嘱咐我们:“中国歌剧•定要以戏曲为基础”,可见他对戏曲的重视。中国的戏曲有着悠久的历史,犹如海纳百川,博大精深。它是中国民族声乐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渊泉,是我们反复强调的民族声乐传统。我本人涉足民族声乐事业已经40年了,受到许多戏曲名家的教诲,获益匪浅,深知撇开了中国戏曲就无从谈论民族声乐。所以我要求我的学生不仅要学会一两段戏曲唱段,而且要结合各地方的方言和民歌对地方戏做深一步的了解和研究,这样做对他们的歌曲演唱是大有裨益的。既然如此,那么为什么不能早一点,譬如在学生刚入学的时候就让他们接触一些戏曲的唱段呢?道理很简单,条件还不具备。此时他们的“乐器”尚未修造好,管道还不畅通,如果过早地演唱这类唱段,声音容易挤卡,真假声容易“打架”,没有学会走就想跑肯定要跌交,岂不是“弄巧成拙”。只有经过严格的基础训练后再安排学生演唱这类唱段,他们才不会感到困难,相反却会显得得心应手,挥洒自如。在豫剧《拷红》中有段快[流水],“在绣楼我奉了(哪哈呀哈嗯啊哈)我那小姐严命, (哪哈呀)……”这段[流水]吐字要快、准,字头饱满不拙、轻巧不虚,如果没有前一阶段扎实的基本功训练,是绝对唱不好这字字晶莹剔透、句句铿锵有力的唱段的。
声乐教师对学生声音技巧训练是首要的,但是到高年级后,做为将要成熟的演员来讲,声音技巧就只是用来演唱的工具、手段,而表现歌曲的内在感情方是演唱艺术的灵魂和生命。这个阶段的声乐教师就不能把教学仅仅限于单纯解决学生的发声问题。我以为,此时的声乐教师更应具备一个“导演”的素质,指导学生用他们学到的发声技巧去刻划人物、去揭示歌曲的灵魂,并进一步去拨动听众的心弦。
李莉是我班上的99届毕业生,经过四年的训练,给他打下了比较扎实的基础,她能灵活自如地演唱中外艺术歌曲,如《在我心里》、《紫罗兰》(斯卡拉第曲)、 《阿利路亚》(莫扎特曲)、《春思曲》(黄自曲)等;还能演唱中外歌剧咏叹词,如《我亲爱的爸爸》(选自歌剧(《贾尼斯基基》普契尼曲)、《求爱神给我安慰》(选自歌剧《费加罗婚礼》,莫扎特曲)、《风萧瑟》、《不幸的人生》(选自歌剧《伤逝》,施光南曲),她音质纯净、音色甜美、音域宽、高低音运用自如,二年级第二学期(她是四年制学生)已能演唱风格极强的民歌,如《赶牛山》、《包楞调》(山东民歌)、《绣荷包》、《槐花几时开》(四川民歌),以及改编过的东北民歌《今年梅花开》等等。
毕业曲目我大胆地给李莉选唱了《看秧歌》这首东北民歌。《看秧歌》是一首说唱性很强的东北民歌。早在五十年代歌唱家郭颂就调动了东北语言中的诙谐、俏皮,把它演唱得韵味十足、风趣动听,迷倒了一批听众。在民歌的演唱中,火候要掌握得相当准确,不能“温吞”也不能“过火”。“温吞”了就丧失了吸引力,“过火”则过犹不及,很容易流于“油”、“俗”。李莉是川妹子,演唱《看秧歌》这样地域特点非常强的东北民歌肯定会有相当大的困难,李莉的语言能力很强,相信她经过努力完全能够掌握好东北语言的四声及“儿”化音,唱好这首歌。
《看秧歌》是一首广为流传的情歌。它刻划出年轻美丽的少女对情郎纯真的感情。李莉模样长得清纯靓丽,形体课上曾以《拾玉镯》的表演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应该说她在外形上很接近这个看秧歌的“东北大姐儿”,重要的是此时她的声乐技巧也已打下了较为扎实的基础,做到高音灵巧,低音结实,上上下下挥洒自如,因此在这首说唱性很强的民歌中,她虽然用了很浓的真声色彩,但腔体不因为“说”而挤住,也不因为“说”而失去头腔共鸣。因此她才能在舞台上敢说、敢唱、敢舞、敢演,做到游刃有余,从而塑造出一个既有东北地区粗犷、豪放、诙谐特点,又有别于郭颂风格的李莉式的“俏”大姐儿。
实践证明我没有看错,李莉口齿流利、吐字清晰、音色甜美而又清脆,一连串几个“儿”化音唱得不“愠”不“火”,再加上精心设计的眼神和身段,准确地表现出人物的“俏”和“媚”,以及她那难以掩饰的兴奋心情。一个聪明、伶俐、娇羞、俊俏而又泼辣、风趣的小佳人儿形象在舞台上脱颖而出。这首歌集中反映了李莉声乐、舞蹈,表演等几门课程的成绩,是各科老师四年来共同努力,辛勤培育了李莉这朵美丽可爱的小“雏菊”。
这些年来学生中有这样一种倾向:喜欢唱大歌,喜欢唱高音,喜欢使足了劲大声嚷。 “他们陶醉在那些他们能发出的很响的声音中。这种人一辈子也成不了真正的歌唱家,尽管他们具有最优越的条件。 (E卡鲁索,引自《歌唱艺术》170页。)他们不知道“唱得高并不意味悦耳动听,因为唱得高时就必然会叫喊……”(M•普列托里乌斯,引自《歌唱艺术》23页。)“人声用中音区部分或是中音区以下的部分来歌唱,比喊高音要好听得多了。” (M•普列托里乌斯,引自《歌唱艺术》23页。)当然,像《孟姜女》中“哭倒长城八百里,只见白骨漫青山”,还有《黄河怨》的最后一句“你要替我把这笔血债清还”等悲愤欲绝的唱段,表现的是不同时代被压迫的女性,对万恶的旧社会的满腔愤懑、对日寇及反动的统治者的强烈仇恨,她样的哭诉有巨大的震撼力,哭倒长城,激怒黄河,用那势不可当的声威将罪恶的旧世界埋葬。然而,并不是所有的歌曲都需要如此,大声的疾呼、强烈的哭诉只是诸多表现手段当中的一种,不能曲曲用、句句用、字字用,那样反而起不到它的战斗作用。我们的歌唱艺术魅力不仅仅在强音,特别是在学生的训练过程中,发声、呼吸、共鸣各方面的基础都不很扎实,过多地演唱这些力不从心的歌曲使声音失去弹性,会使嗓子唱出毛病。
我院研究生班学生黄霞芬是造诣很深的苏州评弹演员,多年来一直钻研借鉴科学的发声方法开拓评弹演唱艺术。在教学过程中我感受到她的演唱内在、含蓄、深刻、沉稳。在《永远的江南》(秦逸、晓权词、吴旋、黄霞芬曲)中,她那徘恻缠绵的柔声细语让我们仿佛看到了雨雾蒙胧的枫桥夜色,那高亢激昂的声音又让我们领略到“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的磅礴气势。“那吴侬软语会化成雨……”中“吴侬软语”四个字音域较低,她唱得很轻。如诉般的低吟,像一缕游丝,但根基很深,不飘不浮,使最后一排的听众也能清晰可辨。苏州姑娘娇嗔柔媚的形象展现在我们面前。
那柔声细语、如醉如痴,正如歌词所叙述的,“滞湿你的心,不肯说再见”,“缠住您的心,让你永留连”。
轻柔的声音需要扎实的基本功训练,对于初学的或低年级的学生来讲困难是很多的,就不能盲目地追求轻柔,必须让他们唱扎实以后,才能够谈得上运用这个魅力无穷的技巧。
人们在谈论艺术的时候不可避免地要涉及一个非常熟悉的词汇——“节奏”,时间艺术讲求节奏,空间艺术也讲求节奏。那么什么是节奏呢?无非是速度的快慢、声音的高低、音量的大小(强弱),光线的明暗、色彩的浓淡(冷暖),画面布局的疏密……等等,等等。一句话:“对比就是节奏”。黄霞芬演唱的《永远的江南》之所以那么悦耳、那么动情、那么引人人胜,除了天赋的一副甜润的歌喉以外,恐怕应该说正是她恰当地运用了声音力度的对比和变化,才会取得如此的魅力。如果没有歌曲前面的抒情委婉、柔美细腻的层层铺垫,绝不会有最后一句“江南,永远的江南”那样的慷慨激昂、那样的酣畅淋漓。反过来,恰当、熟练的技巧运用,要靠扎扎实实的基本功做支撑,基本功是演唱的基础。
谭萍

金秋赏菊乐趣无穷,确是人生一大享受。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得到了超凡脱俗的恬淡心境,我虽没有五柳先生那般洒脱,却也从赏菊中得到了不少感悟和启迪。
看那菊花,不同的品种,不同的花色,不同的造型,不同的花期它们的形态几乎每时每刻都在发生细微的变化。那大朵的“大白积雪”、“云星黄鹤”、“醉舞杨妃”花色艳丽,花瓣肥厚,瓣瓣偎依,层层环抱,相互簇拥着宛若雍容华丽的贵妇人。另一旁的白色或浅黄色的一簇就迥然不同,不仅花色清淡而且花瓣细长,显得灵秀雅致,特别是顶尖部位略呈钩状,酷似古代妇人裙裾上临风的飘带,伸展开来是那么飘逸潇洒,婀娜多姿,活脱脱一个个楚楚动人的古典美人,无怪乎培养它们的花匠给它们起了“丝路花雨”、“千金一笑”、“黛玉葬花”这样俏丽的名字,仔细品味起来可说是惟妙惟肖了。就在人们不知不觉当中,那些似开未开的蓓蕾就像是电影升格拍摄的慢镜头一样,舒缓从容地绽露出它们娇羞的面容,让人搔首踟蹰、流连忘返。当然,引人入胜的不光是这些大“美人儿”,雏菊、悬崖菊等小朵的菊花也被花匠们别具一格地造就出各式各样的形象,一朵挨一朵多像是孔雀开屏,又像是一把把撑开的大花伞,再不就是那高出峻岭之上飞泻而下的瀑布,足以使人浮想联翩。
菊花原来不过就是一些野生的小花,经过几百年多少代花匠选种育苗、剪枝嫁接,精心地栽培,才培育出今天这么多的优良品种,如今它已被选定为北京市市花,为更多的人所赏识。
自然,我不是园艺家,我的这篇文章也不想论述花卉的栽培。不过,我想栽花和育人是同样的道理,做为一个声乐教师我要总结的是如何培养更多更好的声乐人材的问题。但是一提起笔来就自然而然想到了花,这大概是因为在很多场合被人们称做“园丁”的缘故。观花的归途上我常想,做为教师我们本来就应该是一名花匠,我们的工作就是为国家为人民培育妩媚多姿、色彩纷呈的“鲜花”当然不光是菊花(尽管菊花本身就包含了数不清的品种),还有牡丹、芍药、月季、蔷薇、玫瑰、芙蓉、腊梅、茶花、桃花……还有从国外引进的樱花、郁金香等等,等等。学生就像是一个个花骨朵儿,我们要给他们适时适度地“施肥、浇水”还要给他们“剪枝、除虫”,让他们在我们民族声乐这个大“花园”里,茁壮成长,“竞相开放、争奇斗艳”。
不知哪位名人说过这么一句话,“世上绝对没有完全相同的两片树叶”,学生也如此,存在着差别,我们只有承认这个差别,才能根据不同情况因势利导,有的放矢地制定教学计划,这就是古代圣贤提倡的因材施教。
由此我想到了已故的戏剧大师,著名的戏剧教育家王瑶卿先生,众所周知王瑶卿先生为中国戏曲的改革和发展做出了伟大卓绝的贡献,成就斐然,四大名旦皆出自他的门下。但他们不是王瑶卿的翻版,更不是王瑶卿的克隆。梅、尚、程、荀风格迥异,各有所长,形成了各自的流派,流传至今,对于京剧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我以为艺术教育不应该存在什么一成不变的“模式”,如果学生都像“一个模子磕出来的一样”那绝不是成功的教学。实践证明声乐教学没有“包治百病”的“仙丹妙药”,我推崇“一把钥匙开一把锁”,而这把钥匙就深藏在学生的心里。
有个别老师在教学不顺手的时候,很不情愿在主观方面,也就是在自己的教学方法方面找原因,总是爱抱怨学生的基础如何低,条件如何差。目的无非是为自己的无能进行开脱,借以掩饰自己的窘迫。殊不知他(她)这样做的结果将会极大的伤害学生本来就十分脆弱的歌唱心理,是非常要不得的,事实上,作为声乐教师,在学生身上找缺点,挑毛病,是再容易不过的事了。然而,如何发现学生的长处,优点,找出他们身上那被掩盖着的,常常被人忽视的闪光点,那微弱的、潜在却又十分难得的素质,将它小心地发掘出来,加以诱导、培育,造就成为有别于他人的特点和长处。这可就不是一件容易做到的事情了,但是我们必须做到。这是衡量一个声乐教师教学水平高低的重要标志。
歌唱家卡鲁索早在本世纪初就大胆地断言, “有多少个歌唱者就有多少种方法,同时,这些方法中的任何一种(即使用得再正确不过)也可能对其他任何人都是不适用的。假如有人想问我这样的问题,那我就要这样回答:即使我事实上是有一套特别的唱法,它或许也只适合于我一个人。”(引自《歌唱艺术》161页。)说到这里我要再一次重申我的观点:一个好的声乐教师就应该善于发现学生的特点,长处。在他(她)固有基础上,根据他(她)自身的条件,引导他(她)最大限度地展现自己的特长,开拓自己的艺术发展道路,以便于将来形成只属于他(她)自己的、独特的艺术表现风格。
我的具体做法是:
1.从头做起,打好基础
新生来自五湖四海,他们之中大多数嗓音条件好,音乐感觉也不错,尽管如此,在他们身上都不同程度地存在一些问题。我要求他们一切都要从头做起,我则根据每个人的不同情况有针对性地制定出具体的教学方案。
一、二年级的学生必须进行严格的、系统而又全面的声乐基础训练,使之具备扎实的声乐基本功。通过不同的练声曲、歌曲使学生气息平稳、呼吸畅通,腔体张开舒服而不撑(也就是打开腔体,顺通后咽壁上的管道),建立很好的、科学的发声习惯。用已故声乐教育家沈湘先生形象的说法就是:“制造一个优质的‘乐器’”。
在这个阶段多选用一些平稳易唱的初、中级教材,无论演唱中外艺术歌曲或歌剧咏叹调,都要和美声专业要求相同,声音连贯,气息平稳、流畅,腔体打开,真假声结合自如。首先必须要求学生
多听多看有关的经典资料,树立起正确的声音观念和识别能力。需要向学生反复强调,借鉴的前提在于学习,不学习就无从谈论借鉴。在这一阶段还要布置学生演唱我国历代传统的艺术歌曲(包括三十年代优秀的艺术歌曲)。在演唱中不仅要求气息好、声音好、共鸣还要求语言好,在这个基础上要求具备一定的表现力。
这个阶段有些学生会产生不同想法:“我是学民族声乐的,为什要唱这么多洋歌?”“我原来能唱《万里春色满家园》那么大的歌,现在光唱一些中声区多的《春思曲》、《你们可知道》(刻鲁比诺的咏叹调)……”等等。针对学生的思想问题,要做他们的思想工作,我对他们说:“要想盖一幢既华丽漂亮又结实牢固的大厦必须打好地基,只有优质的基础才能保证大厦的精美。”他们一旦学进去以后,尝到.了甜头,这时他们又会产生另外一种想法;“我干脆唱美声吧,.老师和同学都觉得我美声唱得不错。”这时我又要给他们做工作,告诉他们学通科学的唱法,为我们民族声乐事业添砖加瓦才是我们的最终目标。为了这个目标,我们要付出毕生的精力。
一、二年级基础训练阶段,无论男女哪个声部,都有相通的共性,那么在三年级后我认为就必须培养学生鲜明的个性。
2.承认差异,因材施教
在众多学生当中,他们的形象不同;有高有矮,有胖有瘦;他们的声音不同;有的嗓门儿大,又宽又亮,有的嗓门儿虽不大,但音色甜美,还有一些学生尽管嗓音条件一般,但唱得很有韵味。此外还有其它一些差异、诸如每个人的个性不同,审美习惯不同,等等。正因为存在以上诸多不同,才形成学生在歌曲演唱中表现出来的不同风格;有的实大声洪、痛快淋漓;有的委婉细腻、柔美动人。
三年级以后,要教学生继承我们民族声乐的传统唱法,特别是戏曲(京剧、豫剧、河北梆子等)。记得35年前,中国音乐学院歌剧系建系时,马可院长嘱咐我们:“中国歌剧•定要以戏曲为基础”,可见他对戏曲的重视。中国的戏曲有着悠久的历史,犹如海纳百川,博大精深。它是中国民族声乐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渊泉,是我们反复强调的民族声乐传统。我本人涉足民族声乐事业已经40年了,受到许多戏曲名家的教诲,获益匪浅,深知撇开了中国戏曲就无从谈论民族声乐。所以我要求我的学生不仅要学会一两段戏曲唱段,而且要结合各地方的方言和民歌对地方戏做深一步的了解和研究,这样做对他们的歌曲演唱是大有裨益的。既然如此,那么为什么不能早一点,譬如在学生刚入学的时候就让他们接触一些戏曲的唱段呢?道理很简单,条件还不具备。此时他们的“乐器”尚未修造好,管道还不畅通,如果过早地演唱这类唱段,声音容易挤卡,真假声容易“打架”,没有学会走就想跑肯定要跌交,岂不是“弄巧成拙”。只有经过严格的基础训练后再安排学生演唱这类唱段,他们才不会感到困难,相反却会显得得心应手,挥洒自如。在豫剧《拷红》中有段快[流水],“在绣楼我奉了(哪哈呀哈嗯啊哈)我那小姐严命, (哪哈呀)……”这段[流水]吐字要快、准,字头饱满不拙、轻巧不虚,如果没有前一阶段扎实的基本功训练,是绝对唱不好这字字晶莹剔透、句句铿锵有力的唱段的。
声乐教师对学生声音技巧训练是首要的,但是到高年级后,做为将要成熟的演员来讲,声音技巧就只是用来演唱的工具、手段,而表现歌曲的内在感情方是演唱艺术的灵魂和生命。这个阶段的声乐教师就不能把教学仅仅限于单纯解决学生的发声问题。我以为,此时的声乐教师更应具备一个“导演”的素质,指导学生用他们学到的发声技巧去刻划人物、去揭示歌曲的灵魂,并进一步去拨动听众的心弦。
李莉是我班上的99届毕业生,经过四年的训练,给他打下了比较扎实的基础,她能灵活自如地演唱中外艺术歌曲,如《在我心里》、《紫罗兰》(斯卡拉第曲)、 《阿利路亚》(莫扎特曲)、《春思曲》(黄自曲)等;还能演唱中外歌剧咏叹词,如《我亲爱的爸爸》(选自歌剧(《贾尼斯基基》普契尼曲)、《求爱神给我安慰》(选自歌剧《费加罗婚礼》,莫扎特曲)、《风萧瑟》、《不幸的人生》(选自歌剧《伤逝》,施光南曲),她音质纯净、音色甜美、音域宽、高低音运用自如,二年级第二学期(她是四年制学生)已能演唱风格极强的民歌,如《赶牛山》、《包楞调》(山东民歌)、《绣荷包》、《槐花几时开》(四川民歌),以及改编过的东北民歌《今年梅花开》等等。
毕业曲目我大胆地给李莉选唱了《看秧歌》这首东北民歌。《看秧歌》是一首说唱性很强的东北民歌。早在五十年代歌唱家郭颂就调动了东北语言中的诙谐、俏皮,把它演唱得韵味十足、风趣动听,迷倒了一批听众。在民歌的演唱中,火候要掌握得相当准确,不能“温吞”也不能“过火”。“温吞”了就丧失了吸引力,“过火”则过犹不及,很容易流于“油”、“俗”。李莉是川妹子,演唱《看秧歌》这样地域特点非常强的东北民歌肯定会有相当大的困难,李莉的语言能力很强,相信她经过努力完全能够掌握好东北语言的四声及“儿”化音,唱好这首歌。
《看秧歌》是一首广为流传的情歌。它刻划出年轻美丽的少女对情郎纯真的感情。李莉模样长得清纯靓丽,形体课上曾以《拾玉镯》的表演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应该说她在外形上很接近这个看秧歌的“东北大姐儿”,重要的是此时她的声乐技巧也已打下了较为扎实的基础,做到高音灵巧,低音结实,上上下下挥洒自如,因此在这首说唱性很强的民歌中,她虽然用了很浓的真声色彩,但腔体不因为“说”而挤住,也不因为“说”而失去头腔共鸣。因此她才能在舞台上敢说、敢唱、敢舞、敢演,做到游刃有余,从而塑造出一个既有东北地区粗犷、豪放、诙谐特点,又有别于郭颂风格的李莉式的“俏”大姐儿。
实践证明我没有看错,李莉口齿流利、吐字清晰、音色甜美而又清脆,一连串几个“儿”化音唱得不“愠”不“火”,再加上精心设计的眼神和身段,准确地表现出人物的“俏”和“媚”,以及她那难以掩饰的兴奋心情。一个聪明、伶俐、娇羞、俊俏而又泼辣、风趣的小佳人儿形象在舞台上脱颖而出。这首歌集中反映了李莉声乐、舞蹈,表演等几门课程的成绩,是各科老师四年来共同努力,辛勤培育了李莉这朵美丽可爱的小“雏菊”。
这些年来学生中有这样一种倾向:喜欢唱大歌,喜欢唱高音,喜欢使足了劲大声嚷。 “他们陶醉在那些他们能发出的很响的声音中。这种人一辈子也成不了真正的歌唱家,尽管他们具有最优越的条件。 (E卡鲁索,引自《歌唱艺术》170页。)他们不知道“唱得高并不意味悦耳动听,因为唱得高时就必然会叫喊……”(M•普列托里乌斯,引自《歌唱艺术》23页。)“人声用中音区部分或是中音区以下的部分来歌唱,比喊高音要好听得多了。” (M•普列托里乌斯,引自《歌唱艺术》23页。)当然,像《孟姜女》中“哭倒长城八百里,只见白骨漫青山”,还有《黄河怨》的最后一句“你要替我把这笔血债清还”等悲愤欲绝的唱段,表现的是不同时代被压迫的女性,对万恶的旧社会的满腔愤懑、对日寇及反动的统治者的强烈仇恨,她样的哭诉有巨大的震撼力,哭倒长城,激怒黄河,用那势不可当的声威将罪恶的旧世界埋葬。然而,并不是所有的歌曲都需要如此,大声的疾呼、强烈的哭诉只是诸多表现手段当中的一种,不能曲曲用、句句用、字字用,那样反而起不到它的战斗作用。我们的歌唱艺术魅力不仅仅在强音,特别是在学生的训练过程中,发声、呼吸、共鸣各方面的基础都不很扎实,过多地演唱这些力不从心的歌曲使声音失去弹性,会使嗓子唱出毛病。
我院研究生班学生黄霞芬是造诣很深的苏州评弹演员,多年来一直钻研借鉴科学的发声方法开拓评弹演唱艺术。在教学过程中我感受到她的演唱内在、含蓄、深刻、沉稳。在《永远的江南》(秦逸、晓权词、吴旋、黄霞芬曲)中,她那徘恻缠绵的柔声细语让我们仿佛看到了雨雾蒙胧的枫桥夜色,那高亢激昂的声音又让我们领略到“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的磅礴气势。“那吴侬软语会化成雨……”中“吴侬软语”四个字音域较低,她唱得很轻。如诉般的低吟,像一缕游丝,但根基很深,不飘不浮,使最后一排的听众也能清晰可辨。苏州姑娘娇嗔柔媚的形象展现在我们面前。
那柔声细语、如醉如痴,正如歌词所叙述的,“滞湿你的心,不肯说再见”,“缠住您的心,让你永留连”。
轻柔的声音需要扎实的基本功训练,对于初学的或低年级的学生来讲困难是很多的,就不能盲目地追求轻柔,必须让他们唱扎实以后,才能够谈得上运用这个魅力无穷的技巧。
人们在谈论艺术的时候不可避免地要涉及一个非常熟悉的词汇——“节奏”,时间艺术讲求节奏,空间艺术也讲求节奏。那么什么是节奏呢?无非是速度的快慢、声音的高低、音量的大小(强弱),光线的明暗、色彩的浓淡(冷暖),画面布局的疏密……等等,等等。一句话:“对比就是节奏”。黄霞芬演唱的《永远的江南》之所以那么悦耳、那么动情、那么引人人胜,除了天赋的一副甜润的歌喉以外,恐怕应该说正是她恰当地运用了声音力度的对比和变化,才会取得如此的魅力。如果没有歌曲前面的抒情委婉、柔美细腻的层层铺垫,绝不会有最后一句“江南,永远的江南”那样的慷慨激昂、那样的酣畅淋漓。反过来,恰当、熟练的技巧运用,要靠扎扎实实的基本功做支撑,基本功是演唱的基础。